揭秘舒淇原生家庭的伤痕与和解之道,深度剖析背后的故事与成长之路!
舒淇分享关于原生家庭、伤口与和解的话题,她谈及原生家庭对个人成长的影响,以及面对家庭带来的伤痛时如何寻求和解,舒淇强调,每个家庭都有独特的故事和挑战,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面对并克服这些困难,她鼓励大家勇敢正视过去的伤痕,学会与自己和解,从而实现内心的成长与和谐。
雾蒙蒙的城市里,一个内向、怯懦、迷茫的女孩走来了。她家里有个总是醉醺醺、经常对妻女施以拳脚的爸爸;在婚姻里内耗却无法离婚,再把自己承受的委屈转嫁到女儿头上的妈妈以及敏感于不被爱、只能被迫学会“懂事”的自己。这是舒淇导演、编剧的电影《女孩》中的故事,其中的女主角林小丽身上也有一部分她真实的自己。
十几年前,导演侯孝贤鼓励舒淇写出自己的故事,她认真思考了一下,发现“我那个年代的小朋友包括我自己,确实挺有故事性”。如何把亲身经历过的痛苦变为力量,或许是很多东亚女孩一生都在寻找的答案。舒淇在记忆里提取了那些印刻最深的碎片,花10年时间打磨剧本,用自己经历过的苦难搭建了一座“花园”,在此过程中,与自我、与母亲和解,并用一个女孩的故事,安慰所有女孩——你看,这也许是糟糕的一天,但不会是糟糕的一生,已经有一个女孩从梦魇里一步步逃离,长成了还不错的大人,甚至攒足了勇气,转身拥抱从前的自己,她虽然无法忘记从母亲那里飞来的刀子,但她让自己理解了母亲。
这是舒淇以导演、编剧身份创作的首部电影。凭借这部作品,舒淇拿下第30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,并入围了第82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。11月初,《女孩》在全国正式上映。
舒淇以导演的身份携电影《女孩》参加多伦多电影节。本文图/受访者提供
“你要不要试试做导演?”
最初的灵感来源于2009年舒淇与导演侯孝贤的一次谈话,原本在探讨表演的困惑,侯孝贤突然问:“你要不要试试做导演?写自己的故事。”“哈?这样子……我可以吗?”此前,舒淇从没有当导演的想法。“可以啊,拍一个电影并没有那么多的框框。你想要去拍去做,这才是重点。”侯孝贤的一句鼓励,成为她动笔的契机,最初不懂怎么写剧本,那就按侯孝贤告诉她的,从最熟悉最想表达的内容开始。断断续续10年,剧本不断被推翻、重新修改。“一度想过放弃,还好最终没有。”舒淇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2023年,舒淇以评委的身份参加威尼斯电影节,接连观看众多佳作后,突然感受到一股冲动,决心不再拖延:“我觉得如果再不拍,这个戏可能就不会拍了,我就不会做导演了,必须一鼓作气赶快弄出来。”担心自己做不到,舒淇特意找了个监督者——她拨通监制过《大佛普拉斯》等影片的好友叶如芬的电话:“我要做导演拍一部戏了,你来帮我吧,明年暑假开拍。”“真的假的?”叶如芬有点不敢信,“那等剧本写好再说。”舒淇回答:“给我半个月时间。”
话说出去了,非倒逼自己写出来不可了。完成评委工作后,舒淇留在意大利,住进米兰一家酒店闭门不出,原计划15天完成,最终在13天内完成了这部断断续续拖延了10年的剧本。
最终呈现的影像里,有很多向侯孝贤致敬的符号,有些是有意为之,例如从小丽妹妹书包里飘出的红气球,它从地下隧道一路飘摇,慢慢向着自由广阔的天空而去,既是小丽心情的伏笔,也是向侯孝贤《红气球之旅》致意。还有一些细节,在舒淇看来,则像是冥冥中的某种“天意”。拍摄几个机车少年载小女孩们出去玩时,舒淇原本想让他们去溜冰场,她很喜欢溜冰的意境。“在那里,人和人的触碰很微妙,溜冰又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感。”她说。可是如今,已经找不到可以体现40年前状态的冰场,如果搭一个出来,又太浪费钱,于是改成骑机车夜游山路,拍到这部分,舒淇猛然想到侯孝贤的《南国再见,南国》中摩托车行驶在乡间小路的长镜头。
舒淇凭借导演电影《女孩》斩获第30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。
2001年,舒淇曾参演侯孝贤导演的《千禧曼波》,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她演艺生涯的转折点,从这部电影开始,她逐渐摆脱早期的商业标签,转向更具艺术深度的作品。其中有一场经典戏份在“曼波桥”上拍摄,这座“曼波桥”,在舒淇拍摄《女孩》时,以出乎她意料的方式出现了。舒淇记得,那时她正在为小丽母女间追逐的一场戏选景,希望找到一段岔路,让妈妈和小丽争吵之后一前一后经过那个地方,随后两人再分道扬镳,母亲转下楼梯回到自己家庭的原点,小丽继续向前,暗示两人交错的宿命和女孩勇敢奔向自己的人生。
在取景地基隆中山路附近转来转去,真的在一个菜市场附近找到了合适的岔路,正好有一级可以让母亲走下去的台阶,舒淇先走了一遍妈妈的路线,然后继续向前,想看看小丽会走到哪里。才向前走了十几米,她赫然发现,面前正是“曼波桥”。“我当时鸡皮疙瘩整个起来了,浑身发麻。”舒淇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感慨,“这也太夸张了!我觉得这真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,一个很大的缘分。”
于是,在这座“曼波桥”上,25年前《千禧曼波》里的Vicky(舒淇饰演)回眸凝望,25年后,小丽从这里逃离自己的原生家庭。时空交错,在有意和无意间,舒淇用数个影像语言致敬了对她影响至深的导演侯孝贤,完成了华语电影两代电影人之间的对话和传承,而她也从镜头前被导演塑造的演员,走到了镜头之后,成为那个掌镜的、独立表达的导演。
“在成为母亲之前,她也是小孩”
和多数初执导筒的新导演的作品一样,《女孩》是一部带有导演自传性质的青春物语。在舒淇成长的20世纪80年代,台湾经济正待起飞,城市都在改造建设中。在她记忆里,小时候从窗户看出去,天空都是灰蒙蒙的,整个世界好像弥漫着一层雾气,让人没办法停下来好好休息,更不可能思考生活是什么。父母亲都在为生活奔波,一刻也停不下来,他们没有精力去顾及家人的感受。舒淇回忆:“那是一个‘新’与‘旧’正在过渡的时期,传统和现代的交界处,最传统的那个社会的影子还没有消失,还处在边缘。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候,家庭以及孩童都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。”
电影《女孩》海报
也许是这个原因,成长期正处于台湾20世纪80年代的艺术创作者,很多人的作品中都存在一位酗酒且对女人和孩子施以暴力的父亲。例如电影《小雁与吴爱丽》,例如周杰伦的歌曲《爸,我回来了》——“不要再这样打我妈妈,难道你手不会痛吗?”
在舒淇看来,这样的暴力并不局限于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,直到现在,仍然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存在着,只要一个女人没有经济来源,需要依附于男人,那么她就有很大概率遇到暴力,她的孩子就会和她一样生活在暴力的阴影中。就像影片中的女人和小丽,听到父亲归家的摩托声,小丽马上惊恐地躲进简易衣柜,常被男人拳脚相向的母亲,无论白天黑夜都要辛苦劳作,丈夫的缺席让她全权承担着照顾孩子的职责,她的无助、委屈和苦楚像瘟疫一般传递给了孩子——钱包里少了钱,母亲不分青红皂白地体罚小丽,忘记带午餐,她就在全班同学面前掌掴女儿。这些情节的创作灵感,部分来源于舒淇的真实经历。
舒淇1976年出生于台湾一个贫穷的家庭,她曾说自己没有童年,总要小心翼翼地观察爸爸妈妈的反应,如果他们今天心情不好,就离远一点,不然很容易挨打挨骂。她小时候常常躲进衣柜,只要听到爸爸的摩托车声,就马上躲起来,“爸爸看不到我,就不会把我抓起来打了”。影片里面小丽的躲避没有成功,仍被爸爸抓住,但舒淇笑着说自己小时候是成功了的,“那时候爸爸喝太醉,看一圈,呃,怎么没有人,也就走开了”。
有没有过恨意?一定是有的。“小时候不懂事嘛,就会觉得,为什么这个世界要这样对我,为什么爸妈要这样对我,我一定不是他们亲生的。”但是几十年后的今天,当镜头复现当年经历过的画面,却没有怨怼和责备,而是温柔、同情地凝视,尤其对妈妈。开拍不久,有一个长镜头,女人送两个孩子上学回来,洗衣、洗碗、收拾房间……当舒淇在监视器里看到女人干完所有家务,一瞬间肩膀塌下去的背影,她哭了。她“看见”了当年的妈妈,她一瞬间明白,“妈妈不是不爱你,是她太累了。她不是不想温柔,是没力气温柔”。
舒淇出生时,妈妈只有18岁。“她自己都还是一个小孩!”舒淇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感慨,年纪轻轻就承担起沉重而艰辛的母职,妈妈对此毫无经验与准备,不懂得怎么教育孩子,因为她没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,更没学会如何表达爱,因为她自己也没被好好爱过。生活太重了,压得她喘不过气。她的青春、梦想和笑容全部被现实消磨,只为撑起这个家。在釜山电影节的记者发布会上,舒淇哭着说,原谅妈妈了,不是因为妈妈变好了,而是她终于懂得,当一个女人成为妈妈,她的命就变了。
电影《女孩》剧照
这种“看见”构成了影片最刺痛的共鸣。小丽母亲的人生是时代女性的典型缩影:只念到中学就离开学校,白天在发廊劳作,有时还得忍受男顾客的“咸猪手”,夜晚做手工贴补家用,面对丈夫的暴力只会默默承受,将生活的重压转化为对女儿的严苛与疏离。舒淇没有将母亲塑造成扁平的“施害者”,而是通过细节勾勒出这个女性的无助与绝望。她对女儿的责罚,其实是一种心理层面的自我否定——不希望女儿成长为另一个自己。
影片没有回避东亚母女关系的复杂,就像舒淇说的,“以前那个年代母女之间的感情非常奇怪,很纠结,很撕裂,明明是爱,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要刀刃相向。内心里面的温柔,表现出来却是难听的话语和伤害”。这爱里,带着怨,带着伤,带着不舍和亏欠,爱与渴望由她而生,委屈和压抑也因她而起。舒淇没有刻意放大这种既想逃离又想依赖、挣扎且痛苦的关系,只是平静地注视这份母女之间摇摇欲坠却又坚韧的感情。
写剧本时,舒淇始终站在小丽的立场写一个女孩的故事,可是等到电影拍完,后期完成,再好好回看这部片子,她突然发现,自己的关注点已经不在小丽,而是放在了母亲身上。
小丽对妈妈并没有真正地怨恨。虽然妈妈打她,惩罚她,她只是觉得疼痛,而不是恐惧。隔着一道铁门,小丽问妈妈:“妈,你和他离婚好不好?我们一起走好不好?”
“我以为我好了,其实伤口还在”
妈妈没有和小丽一起走,因为爱,她把孩子送去了亲戚家。而舒淇是自己离家出走的,16岁那年,为了逃离家庭中的暴力,她开始了独自谋生之路。如今回看那段日子,她觉得自己像一条漂泊小船,哪里可以靠岸就靠岸,但好在并没有迷茫。可能因为很早就出来谋生,舒淇觉得自己一直是个活在当下的人,离家出走需要赚钱养活自己,那就马上找个咖啡厅端盘子,内耗没有用,有用的是解决眼前的问题。
第一次当导演也是这样,她怎么都记不起来第一次坐在监视器后的导演椅上是什么感觉了,没有人们想象中的忐忑,甚至没顾上感受什么心情。“一喊action就马上进入那个世界,喊cut后,又要马上调整各种细节。第一次坐导演椅?完全忘记这件事了。”在舒淇看来,作为演员,只要待在人物的状态里就好,但是导演不行,导演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,有太多事情要处理,站在一个更抽离的角度,眼睛里全是问题,“这个碗不对”“那个时钟不行”……给演员讲戏的时候需要感性,处理现场问题又需要理性,好像“一边做语文题一边又解数学题一样”,“快要精神分裂”,在不断“解题”中,第一部戏就这样拍下来了。
第一个版本剪完,长度近4个小时,舒淇给小丽的父母都建立了完整的故事线。9m88(汤毓绮)饰演的母亲在学校被霸凌,被原生家庭抛弃,不得已早早进入社会,婚后又受家暴,是一个可怜却仍勇敢面对生活的女人;邱泽饰演终日酗酒的父亲也并非单一的恶人,而是原本家境殷实却因为意外而阶层滑落,又被社会压力压垮的男人。但因为篇幅限制,只能舍弃那些故事,回归到最主要的女孩身上,影片长度也压缩到2小时。
最难处理的部分,是尾声,舒淇记得侯孝贤告诉过她,“拍电影只是揭露故事的冰山一角”。她的剧本结束在男人出车祸,但是制片人叶如芬觉得停在这里太突然了,之后妈妈怎么样?小丽过得好不好?影片需要一个更“好”的结尾。舒淇苦苦思索了两个月,眼看开拍在即,某一天,她坐在书桌前,盯着窗外摇晃的树影,灵感突然来了。
最后一幕,已经成年的小丽回家探望母亲。母亲守着无甚变化的家庭陈设,还有已故丈夫的灵位,独自在家。尴尬的沉默、局促和已经无法跨越的鸿沟,是传统东亚家庭里最真实的距离。可是,小丽仍然忍不住问:“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年我过得好不好?”
没有畅快的彼此倾诉,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大和解,仍然是心有不甘的诘问。只是,“过得好不好”,越是简单的问题,越无法简单地回答。有观众留言说,“正是这种不和解,反而让我有被轻轻抱了一下的感觉”,因为痛苦是真的,只有痛苦被看到,才有治愈的可能,但并不代表,一定要原谅,一定要假装无事发生。
舒淇坦言,整个拍摄过程像洋葱般把自己一层层剥开,直视记忆深处的阴暗面:“我以为我好了,可再次触碰时,伤口还在。”“说不上什么放不放下,只是长大后更能理解为什么父母会那样对待自己。”
影片的最后,小丽在眼泪中,吃下一碗母亲为她准备的猪脚面线。她的质问没有得到答案,母亲的道歉或许也永远不会到来,时过境迁,横亘多年的隔阂怎么会在三言两语之间化解,“过去了”不等于“和解了”。可是,既然人生还要向前,那么就这样接受吧,你的痛苦和我的悲伤,都没有答案,更没有谁能拯救谁,但是我们彼此“看见”,那么也许,就胜过了答案。
发于2025.11.10总第1211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杂志
杂志标题:导演舒淇:从痛苦中长出一点勇气
记者:李静
编辑:杨时旸
作者:访客本文地址:https://dszpk.cn/wiki/5404.html发布于 2025-11-07 10:01:03
文章转载或复制请以超链接形式并注明出处武汉财经网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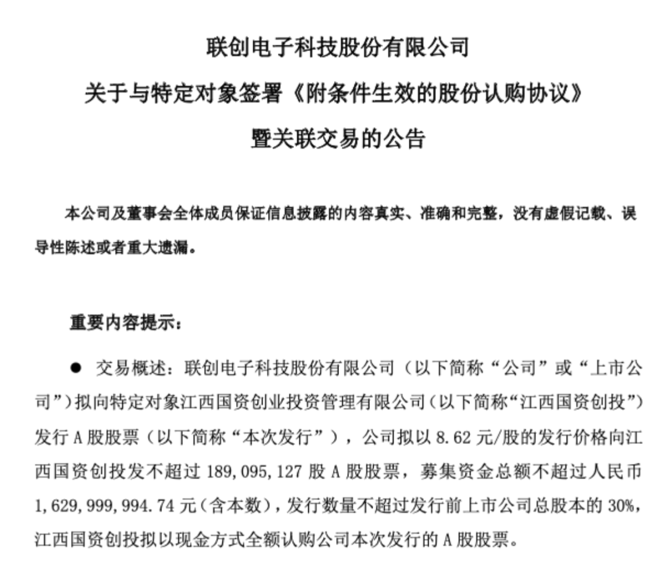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