揭秘植物人背后的乱象,2500亿市场如何暗流涌动?
近日曝光的涉及巨额资金和社会乱象的事件中,有人因各种原因陷入昏迷状态或成为植物人,背后涉及巨额资金问题,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,据悉,这一事件背后存在诸多乱象,亟待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并采取措施,以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和生命安全,这一事件也提醒我们,需要加强对相关行业的监管力度,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。
如今的张雯,再难以回到“未做过任何医美”的状态。
去年5月,24岁的她在北方某市一家私立连锁医美机构花费一万余元,接受了玻尿酸的全脸填充,涉及眉骨、鼻基底、苹果肌等多个部位。她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回忆,这是她第一次尝试医美,就一次性注射了8支玻尿酸。填充两三个月后,其脸部开始反复水肿。她回到该医美机构咨询,医生建议再补打一针玻尿酸,结果肿胀进一步加重。今年9月,她找到医疗机构修复,结果是“脸更肿、更难看”。
张雯尝试的项目属于轻医美。轻医美是一个商业化概念,通常指通过无创或微创手段改善容貌、延缓衰老。由于满足了人们“想变美又怕手术”的需求,这一赛道近年迅速崛起。嘉世咨询今年7月发布的《2025中国轻医美行业现状报告》预测,2025年中国轻医美市场规模有望突破2500亿元,并将以15%—20%的年增速持续扩张,成为全球最具增长潜力的市场之一。目前,轻医美项目已占医美市场的六成以上,且占比仍在提升。
但在行业高速增长背后,消费者期待与轻医美效果之间仍存在落差。许多像张雯一样的年轻人,被“轻风险、快恢复”的宣传吸引,却未必了解每项技术背后的潜在风险。
图/视觉中国
致命风险
做面部填充前,张雯对该项目几乎不了解。
直到今年6月,她才意识到,前述症状由玻尿酸移位与吸水导致。她的遭遇并非个例。在社交平台发帖后,许多人向她私信。多位受访专家强调:“轻医美并不轻,部分项目的风险甚至高于外科医美。”
轻医美主要包括注射类和光电类两大类项目,其中玻尿酸是注射类中最畅销的品类。《2025中国轻医美行业现状报告》指出,以玻尿酸、肉毒素为代表的注射类项目,以及热玛吉、光子嫩肤等光电类项目,是轻医美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,其中注射类占比最大。
上图:2019年11月,进博会上展出的玻尿酸与胶原蛋白产品 图/视觉中国
下图:2021年4月,消费者在大健康博览会上体验光子嫩肤。图/IC
如今,轻医美消费正呈现年轻化趋势。国内著名整形外科医生郭树忠已从业30余年,现任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整形医院院长。他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谈到,过去,轻医美的核心消费群体平均年龄约40岁,近两年,这一平均线已下移至35岁上下。根据前述报告,国内轻医美消费者中,“90后”的占比已超过 50%。
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主任医师杨军指出,热玛吉、超声炮等光电类项目常被误认为“安全系数高”,但若能量输出时间、能量密度或作用部位掌控不当,就可能引发严重损伤,包括皮肤灼伤、水疱、瘢痕增生,甚至真皮层坏死、面神经损伤或毛囊永久受损等不可逆后果。北京协和医院整形美容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智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热玛吉对技术参数要求较高,但市场上假机、翻新机泛滥,烫伤事件频发。
今年1月,28岁的蒋芸因注射了两支价格不菲的童颜针产生排异反应,脸部整整肿胀了一个月。她连打了三天消炎针并服用抗炎药,症状才缓解。那段时间,她几乎无法正常工作生活,出门必须戴口罩。
目前,市面上仍有不少假冒注射类产品流通。杨军指出,不少肉芽肿、肉毒素中毒等医美事故,都与求美者使用假货有关。他强调,只有获得国家批准的产品才算正品,走私“水货”、无资质机构自制产品等都属于假货。
过去两年,王智在门诊接诊过不少出现问题的求美者,多数是在小型私立或不正规机构被“坑”。他提到,一些机构为了节省成本,用获批二类医疗器械注册的胶原蛋白冒充三类产品。
北京市海淀区一家私立医美机构店内的宣传内容 摄影/本刊记者 牛荷
郭树忠指出,假肉毒素的风险同样巨大。肉毒素本质上是由肉毒梭菌产生的强效神经毒素,正规临床使用的“注射用A型肉毒素”需按毒性药品管理。假肉毒素的问题在于实际剂量往往远超标注。肉毒素以“生物单位”计量,需要复杂的生物测定和严密质控,而造假者不会投入这些成本。求美者一旦注射过量,轻则表情僵硬、眼睑下垂,重则出现全身无力甚至呼吸肌麻痹,危及生命。
本刊在实地走访中发现,一些医美机构正大力宣传所谓“骨塑形针剂”。这类产品价格不菲,甚至在部分机构中已成为主营业务。11月3日,记者以消费者身份来到一家私立医美机构,发现前来咨询的求美者络绎不绝。
工作人员刘丽称,“骨塑形针剂”是其所在机构的主打项目,也是销量最好的产品,半脸填充售价19.8万元,全面部填充则高达39.8万元。但记者询问该针剂的具体成分时,她却难以说明,只一再强调是机构自行复配的产品。她还宣称该产品“有批号、材料顶级、效果可维持3—5年”,并展示“前后对比照”以营造明显的“脱胎换骨”效果。
国内某三甲医院一名骨科副主任医师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用于注射的材料首先须取得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,而此类所谓“骨塑形针剂”多属“智商税”,技术含量并不高,其主要成分包括胶原蛋白和羟基磷灰石,后者成本极低。
上图:京东医美北京国贸店内的服务项目与价格 摄影/本刊记者 牛荷
中图:美博会上的美团美容展台 图/视觉中国
下图:新氧青春诊所(北京保利总部店) 摄影/本刊记者 牛荷
记者查阅国家药监局官网发现,国内虽然已有羟基磷灰石骨填充材料获得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,但其批准的适应证并不包括面部软组织填充,使用范围仍限于口腔领域,如牙槽凹陷的填充等。“没有获批适应证的前提下,将其用于面部美容,风险极大。”王智指出。
王智表示,这类“骨塑形针剂”多数为机构私下混配,出现问题的概率不小。事实上,羟基磷灰石与胶原蛋白的混合配方长期未在国内获批,根本原因在于这类材料吸收周期极长、接近永久留存,一旦出现并发症,注射物难以清除,处理难度和风险都极高。
注射项目的安全性不仅取决于材料本身,还与医生的操作技术密切相关。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会长宋建星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解释,越是“结构性、支撑类”的材料,越需注射在皮肤深层;越是“修复、改善皮肤质量”的材料,越应注射于浅层。例如,小分子玻尿酸用于真皮中浅层填平细纹;主要成分为聚左旋乳酸的童颜针,需稀释后注射到真皮皮下层;大分子玻尿酸等则通常注射在骨膜层,用于塑形,如改善鼻梁塌陷。
郭树忠提醒,面部血管分布复杂,深浅动脉交错且互相连通,尤其是鼻部、眼周等区域,是注射的高危地带。医生只能凭经验避险,一旦误入血管,可能导致皮肤坏死、失明、偏瘫甚至成为植物人。部分操作者在培训不足、经验欠缺的情况下贸然上手,更易出现严重后果。
能完全恢复原状吗?
在宋建星的日常门诊中,慕名就诊轻医美修复的患者比例并不低,约占门诊量的15%。郭树忠指出,如今市面上的修复方式五花八门,许多人为修复花费的成本甚至比最初医美时还高。“很多医生过去靠打针赚钱,现在又靠修复并发症赚钱。”
林晓已在医美行业从业近20年,如今是一家私立医美机构的运营总监。自2023年以来,她明显感受到轻医美行业中涌动的修复热潮,且年轻群体占比更高。市面上已出现专门从事轻医美修复的机构。林晓提到,相比光电类项目,注射类项目的修复难度更大。有些机构甚至把某一类副作用细分成单独业务,比如专门修复馒化。
馒化是注射类项目最常见,也是较为严重的并发症之一。郭树忠解释,玻尿酸、脂肪等材料具有吸水性,注射后会让面部变得饱满;但若单次或累计注射量过多,面部便可能出现浮肿,看起来像馒头一样。
在郭树忠的门诊,近年来,馒化修复病例持续增多。林晓发现,许多出现馒化的求美者,是因为在不同机构、不同时间注射了多种材料,导致面部材料堆积过量。当她们回忆使用过哪些材料时,往往已不清楚具体成分、注射部位甚至注射机构。
张雯遭遇的情况也属于馒化。今年9月,她在一家机构注射了三针溶解酶,以分解注入面部的玻尿酸,共花费2100元。她回忆,医生原本计划为她做全脸溶解,但由于无法确定玻尿酸移位的具体层次,只能溶解部分区域。
杨军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,对于无法确认自身注射材料的人,修复难度更大。因为不同材料产生的并发症,处理方式完全不同。例如,分解玻尿酸需要使用溶解酶;某些生长因子类项目的并发症,一般可通过激素类药物等针对性治疗。林晓补充,修复时注入的溶解酶在皮肤组织中的扩散与反应存在很大不确定性,对医生技术与经验要求极高。
多位专家表示,馒化后的面部想要完全恢复原状几乎不可能。郭树忠介绍,除了使用溶解酶,还可以通过热玛吉、超声炮等促进材料吸收,或采用材料取出手术,清理面部组织中的再生类材料。
杨军表示,人体皮肤组织结构复杂,从表皮、真皮到皮下组织,再到肌肉、神经、血管、骨膜,层层交错。假设人的面部皮肤组织像一本上千页的书,注射材料打进去时可能恰好打在第500页,也可能在第700页,但之后材料可能在不同页码间扩散,医生难以完全精确定位并清除。
材料取出手术的代价也不小。郭树忠称,有的患者需要掀开眼皮清理内部物质,再重新缝合、收紧皮肤;若清理后造成皮肤松弛,还需同步进行拉皮手术。业内对于注射材料的取出手术一直存在争议。多位专家指出,医生通常不会轻易建议患者进行此类修复。
除了馒化,注射类项目的修复需求远不止于此。王智在门诊中常见从外院修复失败过来求助的求美者。他提到,这些患者大多在为几年前做的项目“买单”。有人因感染导致面部出现大片流脓斑块;有人的太阳穴填充不仅没变饱满,反而出现肿胀、流脓,形成更深的凹陷。王智表示,一些求美者注射填充材料出问题后,机构要么敷衍,让患者热敷;要么直接推诿,让他们去医院。更糟的是,有些机构甚至完全失联。
在林晓看来,注射类项目之所以造成不可逆的损害,与部分求美者较为激进有关:她们追求“立竿见影”的效果,当出现并发症后,又渴望彻底修复,这种被焦虑放大的心态,往往会引发新的问题。与此同时,一些医生也容易被商业利益裹挟。
郭树忠指出,社会竞争不断加剧,年轻人的外貌焦虑随之上升。许多女性出于职业和婚恋压力选择抗衰项目:一方面,部分职业偏好年轻面孔,外表成为竞争力的一部分;另一方面,婚恋压力使她们更在意外貌,以保养年轻来增强自信。
“这其实指向一个更深层的议题:如何找到最合适的平衡点。”林晓说。
“医美的核心是‘医’”
林晓见证了医美行业从早期的野蛮生长,到如今竞争白热化的全过程。其中,最直观的表现便是价格的全面“内卷”。
今年以来,新氧、美团、京东等平台在轻医美领域掀起了降价潮。其中,新氧动作最大,通过与上游厂商的定制合作,将原本单支动辄上万元的童颜针压到2999元。一些上游厂商也在主动调整策略。
联合丽格医疗美容集团创始人、董事长李滨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分析称,医美行业的底层逻辑决定了它逐渐演变为以产品为中心的市场。这种模式使机构变成了单纯的“产品销售店”,医生被异化为产品的销售工具。“这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医生的作用与价值。”
李滨指出,国内许多私立机构中,医生并不掌握主导权,咨询师和设计师等销售属性的从业者在治疗环节中话语权更高,甚至能决定求美者的治疗方案。这些人员大多没有医学背景。“这意味着在一些私立机构里,医生不承担实质医疗责任,从而容易引发医疗事故。”“市场的注意力被产品与噱头占据,却忘记医美的核心是‘医’。”林晓说。
即便在公立医院体系,风险也同样存在。郭树忠介绍,出现问题的操作者中,既有来自公立医院和正规私立医美机构的医生,也有不规范的黑医美从业者。“技术好、经验丰富的医生确实能降低风险,但无法完全避免。”
陈玉林是国内一家三甲医院整形外科的副主任医师。他表示,目前,从事注射类操作的医生整体水平不容乐观。他所在医院曾与其他医院联合举办过面部解剖的培训班,但招生面临两难:如果门槛设得太高,如只招主治及以上职称医生,几乎没人报名,因为其已有了稳定工作与病源;而报名者往往来自其他科室转行、非医师出身,或私立机构的医生,导致培训质量难以保障。
在林晓看来,医美从来不是简单的“打产品”,而是一个完整的医疗过程。经验丰富的医生需在治疗前评估面部结构和合理用量;治疗中掌握注射层次和技术;治疗后还需能及时发现并处理问题。如果机构具备完善的售后体系,医生与美学顾问持续跟进,许多问题可能得以在“黄金修复期”得到解决。
“医美乱象的根源在于,国内的监管和法律法规尚不完善。”李滨指出,虽然近年来国内医美领域的监管举措不断,但长期呈现“运动式治理”特征:一旦媒体曝光,相关部门便迅速行动;但风头过后,整治力度随之减弱,难以形成持续、有效的监管机制。而行业缺乏标准和规范,也导致各种模式应运而生,例如渠道模式、代理模式等。
他还表示,医美行业现行规定多沿用医疗领域标准,难以适应医美这一消费型医疗的特殊性。例如,责任认定和医疗中介的合法性等关键问题长期处于法律灰色地带,导致中介行为无序发展,高额返佣泛滥。“当规则的缺位成为常态,最终为每一次‘冒险’买单的,终究是一个个具体的、渴望变美的人。”
(文中张雯、林晓、蒋芸、刘丽、陈玉林为化名,实习生刘孜妍对本文亦有贡献)
发于2025.12.1总第1214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杂志
杂志标题:轻医美的沉重代价
记者:牛荷
编辑:杜玮
作者:访客本文地址:https://dszpk.cn/wiki/6100.html发布于 2025-11-27 10:00:33
文章转载或复制请以超链接形式并注明出处武汉财经网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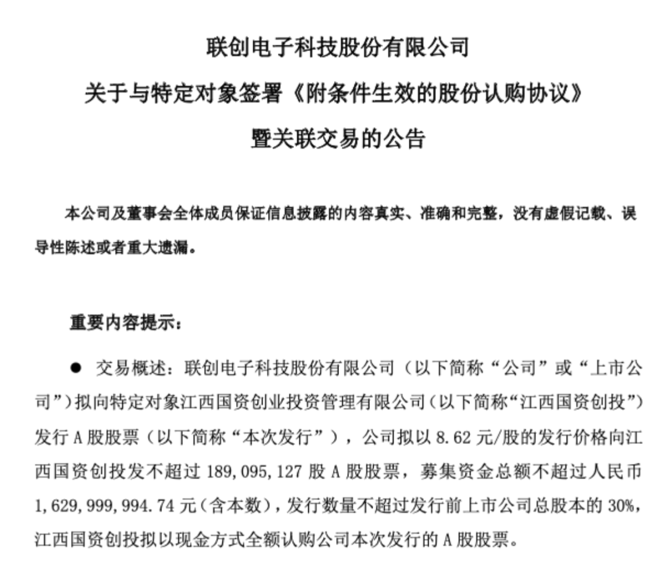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