持有2377万股年薪仅1.2万,扬帆新材樊培仁被留置,公司控制权暂未变
扬帆新材的樊培仁持有2377万股,但其年薪仅为1.2万,最近他被留置,但公司控制权暂时未受影响,这一事件引发了市场关注,目前具体情况尚待进一步披露。
扬帆新材(300637.SZ)的股价在8月26日骤然下挫,开盘后一路下跌,至午间收盘时跌幅达5.61%,报15.15元/股。这波震荡源于前一日公司披露的一则重磅公告:控股股东、董事樊培仁被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监察委员会实施留置并立案调查。消息一出,市场哗然,投资者神经紧绷,纷纷猜测这位实控人的突然“消失”会否引发连锁反应。但扬帆新材迅速安抚市场,强调公司治理结构完善,日常运作稳健——高管团队在董事长樊彬和总裁陶明的带领下正常履职,控制权未生变局。表面平静之下,暗流汹涌。翻看公司2024年年报,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浮出水面:樊培仁去年薪酬仅1.2万元,却手握2377.99万股公司股份;而其子樊彬薪酬高达67.82万元,持股量更达4890.24万股。这组数字的强烈反差,像一把钥匙,悄然打开了公众对公司治理深层矛盾的追问之门。
扬帆新材扎根紫外光固化新材料和含硫精细化工领域,自2002年创立以来,逐步跻身行业前列,并于2017年登陆深交所。其控制权牢牢掌握在樊氏家族手中:樊培仁与妻子杨美意、儿子樊彬通过控股集团及海外公司,合计持股36.50%。家族企业的底色下,权力交接早已悄然完成——樊培仁2017年卸任董事长后,由樊彬接棒至今,自己仅保留董事席位。这种“父退子继”的模式,本是企业传承的常态,但樊培仁的超低薪酬与巨额持股形成刺眼对比。1.2万元年薪,远低于A股上市公司董事平均水平(通常数十万元),甚至不如普通白领月薪。这不禁令人疑窦丛生:是象征性岗位,还是暗藏股权激励或避税策略?抑或是樊培仁已将重心转向幕后操控?反观樊彬,作为现任董事长,67.82万元薪酬虽不算顶奢,却更贴近职业经理人常态。父子薪酬的“冰火两重天”,折射出家族企业内部权力与利益的微妙平衡——父辈低薪持股,或为降低公司成本、规避监管焦点;子辈高薪履职,则凸显现代治理的表象。然而,这种安排是否合规?是否损害小股东权益?当监察委的立案通知书送达,所有猜测瞬间升级为严峻现实。
业绩的转折为这场风波增添了戏剧性张力。今年上半年,扬帆新材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:营收飙升至4.73亿元,同比增长47.93%;净利润2313.72万元,成功扭亏为盈。公司解释,这得益于光引发剂下游PCB(印制电路板)和涂料行业的复苏,产品需求回暖和价格抬升共同发力。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——2023年同期,公司还深陷2123.85万元的亏损泥潭。行业东风确实助力扬帆新材扬帆起航:全球电子产业回暖推高PCB需求,环保政策倒逼涂料企业转向紫外光固化技术,公司作为上游核心供应商自然受益。但业绩高光难以掩盖调查事件的阴霾。樊培仁的留置,绝非孤立个案。近年来,随着反腐风暴席卷资本市场,上市公司实控人涉案屡见不鲜,动辄引发股价地震甚至控制权崩塌。扬帆新材虽宣称“治理完善”,但樊培仁作为控股股东兼董事,其涉案性质尚不明朗。若涉及经济犯罪或信披违规,可能触发监管连锁反应——股权冻结、质押爆仓、董事会动荡等风险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。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市场信心:投资者已用脚投票,股价单日重挫近6%,反映出对家族企业“一言堂”治理模式的深度担忧。毕竟,当实控人薪酬微薄却持股庞大,其利益与公司绑定更似“赌注”而非“责任”,一旦个人问题爆发,公司极易沦为牺牲品。
这场高管低薪谜团与留置风波的背后,是中国民企治理转型的阵痛缩影。扬帆新材的案例,暴露了家族企业“去家族化”的步履维艰——尽管樊彬代表新一代接手经营,治理架构看似现代化,但父辈通过股权保留终极控制权的手段,仍与现代公司治理的透明、制衡原则相悖。低薪酬或为降低公司费用、美化报表,却也可能弱化高管问责机制,滋生“影子操控”。值得玩味的是,行业复苏的东风恰逢其时,为公司提供了缓冲垫。紫外光固化材料作为“绿色化学”代表,正迎来黄金期:全球市场规模预计2025年突破千亿,中国政策强力扶持。扬帆新材的技术积累(如光引发剂合成专利)是其护城河,但能否持续受益,取决于治理乱局能否迅速厘清。若调查延宕,恐拖累研发投入与客户信任,尤其在国际竞争加剧的当下,巴斯夫等巨头正加速布局该领域。投资者须警醒——低薪高管的高持股,往往伴随股价波动敏感症:一旦负面消息发酵,抛压可能远超预期。而樊培仁留置案的走向,将是最大变量。乐观看,若调查仅涉个人事务且快速结案,公司凭借业绩弹性或能收复失地;悲观看,若升级为重大违法违规,不排除控制权重组甚至退市风险。这一切警示我们:上市公司治理不能止于口号,股权结构透明化、薪酬机制合理化才是抵御风浪的压舱石。
作者:武汉财经网本文地址:https://dszpk.cn/wiki/2533.html发布于 2025-08-26 14:09:59
文章转载或复制请以超链接形式并注明出处武汉财经网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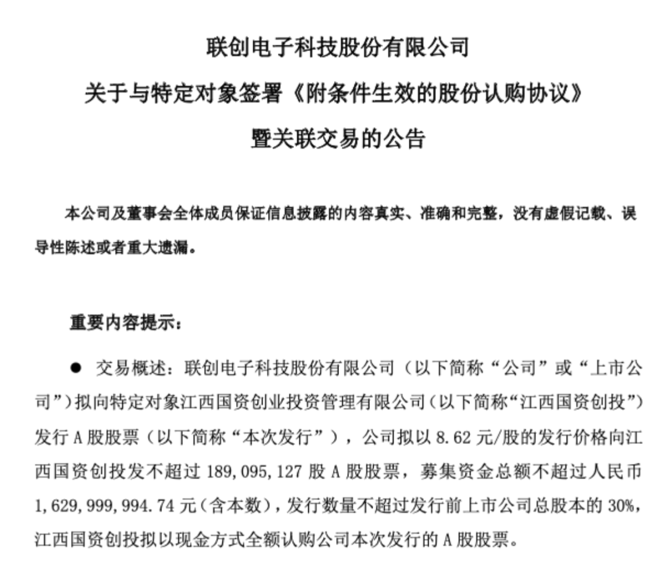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